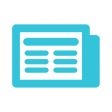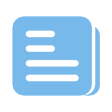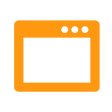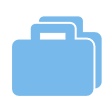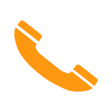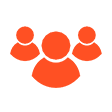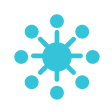当前位置:首页 > 检察文化
当前位置:首页 > 检察文化
一个初秋的夜晚,风停了,雨还在下。屋里已有一些凉意,但是这样的天气我仍然喜欢敞着窗户睡觉,身边孩子细微的鼾声在提醒我夜已深,然而总有一些时候想睡却睡不着,雨滴就像在枕边落下,清晰地让人不得不用尽全力去关注大自然的瞬息万变,城市里的夜晚也如此安静。思绪好似一缕浮云飘来飘去最终竟停留在了儿时一个盛夏晴朗的夜晚。
夜晚睡觉前姥姥依然用粉笔状的“灭虱灵”在床单上来来回回的划拉,直到那“粉笔”下去了小半截。用点着的艾草枝在屋里熏上一阵子,然后关门离开茅草屋,到上屋门廊的小木凳上乘凉。
之所以叫上屋是因为它相对于敞院的另一间砖瓦房(下屋)与茅草屋来说的。它背靠山脊,需要爬三四级不规则的青石台阶才能到达。爬上台阶,青石板做基,泥土做坯的长方形房屋赫然于眼前。石阶上面有一个门廊,由两根结实的楸木柱子做支撑,坡屋顶的瓦片一直延伸到柱子的外缘。门廊一侧的尽头处置有矮墙,矮墙遮蔽之处是黄泥盘成的柴灶,柴灶附近仍有晚饭后仍未散尽的余温。门廊正中间是上屋的门,门顶上有一盏黄色的灯泡,这盏灯并不常开,偶尔会给晚归的人带来一些慰藉。
敞院渐渐地淹没在夜色中,傍晚低空飞行的蜂鸟的嗡鸣声渐渐远去了,各类鸣虫的切切私语声逐渐的清晰起来。偶有一只嘶嚎的蝉从树上落下一头撞在地上,在院子里嘶嚎,试想它可能折了翅膀亦或生命将尽做最后的挣扎,明天再不能起飞。山谷里异常寂静。柴火炉灶中烧退了的木柴火星微弱的光将灶底厚厚的草木灰映衬成一片灰白色,随着夜幕的微风,那尚未燃尽的柴火星忽暗忽亮,像一个人的呼吸,更像是一双生动的注视着一切的眼睛。
我喜欢坐在大舅身边,他有一把长杆的土枪,农闲时会打一些山鸡、野兔。他住在上屋,屋里土坯墙的泥眼里插着几根白色、褐色相间的野鸡翎,桌子一角的竹筐里放着一张灰白色的兔子皮毛。他的屋里以及身上永远都有一种采收烟叶时留下的浓重烟油味,他的手上也时常沾着一层不易清洗的黑色烟油。他从不带我去烟田里,也从不让我用手剥那些青皮核桃,生怕染黑了我的手指。他会将青皮核桃放在劈柴的木缘上一手把着核桃,一手用短柄斧子将核桃的外皮转圈砍下,每个核桃只需四下,便可以得到一个近似正方体的囫囵个去壳核桃,用手轻轻摘去核桃隔便会拉扯着核桃内皮及首尾两处面积很小的青皮一起脱下,得到白嫩鲜甜的核桃仁。大舅从来都不知道其实我非常喜欢烟油的味道,我总以为这种味道是一个英勇猎人所特有的味道。等待大舅打猎归来的每个白天或夜晚都让我无比的期待和兴奋。这样的夜晚他会闲坐着给我讲他是如何一整晚跟踪追赶一只被枪击中后仍然负隅顽抗的野猪的故事,我可以边听边踏实的嚼食当天采摘的新鲜五味子作消遣,五味子短胖的肉质果梗上一串串的晶莹小珠子,红色的浆果是酸甜的,绿色的浆果是酸涩的……
姥姥也坐在门墩上想着第二天要吃的饭,馒头是否够吃,瓶子里的芝麻油是否还有一两滴可用……凭着熟悉的烟草味,知道她在夜幕中静静地抽掉了一袋烟。
我听到了牛铃的叮当声,那铃铛的材质、薄厚、做工各不相同,混在一起既嘈杂又悦耳,仿佛把敞院从寂静的深渊中拉了出来,声音越来越近了,终于大家都站了起来……哥哥将一篮子“鸡头根”(黄精)仍在屋檐下,扔给我两个木通果(八月炸),那果子刚好成熟绛紫色的厚皮已经开裂露出了白色的果肉。门廊的灯亮了,泔水饮牛,入圈后哥哥开始狼吞虎咽的吃饭,他急迫的到屋里拿出小收音机想享受一刻的轻松,然而那收音机总是快要没电,或信号不好,勉强的播放一阵嘶撕拉拉的豫剧,他不得不放下汤碗不断地调整天线、拍打电池,直到无奈的关上,敞院在夜色的笼罩下又恢复了寂静。
夜空中的星星很大,很亮,各种星座十分清晰可见,可能还来不及在脑海中想些什么,就要被蚊子的叮咬而着急,并不得不全神贯注的照顾着自己身体每一处裸露的皮肤。大栎树上“梆、梆”的掉下来几个橡实果子,因为带着毛壳落地砸在石阶上发出几声闷响,然后随着一些个跳跃滚落到了山沟里流入溪水中“咕咚”一声,便不再作响。
姥姥领我的手摸黑进了茅草屋,划一只火柴,点亮一盏油灯,罩上污迹斑斑的玻璃灯罩子,在两摞砖头,几并木料垒的木板床上,挪开针线伙计的柳条筐子,抖了抖被子,仍旧用粉笔状“灭虱灵”在床铺上划拉了几处感觉没有划到位的地方,将一个干净的用来挠痒痒的鞋刷子仍在枕头下面,就让我上床了。是时候该休息了,我听到了木门关闭的声音,然后是粗实的木插销滑动的声音,布鞋底子擦过凹凸不平的地面的声音,吹油灯的嘘声,我闻到了煤油灯芯子刚熄灭时冒出来的呛人烟味,所有的光亮都不见了,唯一一个椭圆形的糊着油纸的小木格窗户透着一小片可爱的月光,我依偎在姥姥身边,躲在满是“灭虱灵”呛人而又熟悉的味道中,裹着被子安心的睡着了……
雨渐渐停了,银杏树的叶子上有残存的雨水汇成大而重的水滴,很久才落下来一滴“啪”的一声落在水泥地上。那混着艾草、灭虱灵以及煤油味的茅草房从眼前消失了。真的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红色的坡屋顶砖瓦房,那红砖青瓦也不再是曾经的砖头瓦砾,那崭新的房子似乎与敞院里老旧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它坚硬的墙皮和房顶再长不出温柔的小草和青苔,似乎与这敞院周围和谐的大自然都不相融了。
两年前的清明节我回老家扫墓,我看着那砖瓦房,心里却在不停地勾勒着茅草屋,糊满旧报纸的墙、房梁上被柴火熏得乌黑发亮的苇席顶子、屋内影墙边上那凹凸不平的地面、屋子一角干燥的玉米皮子、案板上装猪油和咸菜的泥瓦坛、存放鸡蛋的小木箱子,还有永远也挥之不去的“灭虱灵”的味道……然而当我推开门的那一瞬间,一切都不是记忆中的样子,那情景让人有种无法言表的失望,我没有继续往里走。一个头发苍白的老人站在牛棚附近兴奋的张望,那人就是我的大舅,他已经年近八十。崭新的砖瓦房做了谷仓,他自己搬到了牛棚旁边的土坯房里居住。我推开房门,土坯房里就一个土炕,一张没有刷油漆的旧木桌子,桌上满是灰尘,放着一个很久不用的煤油灯,低矮的房梁上存着很多寿木板材,房间里仅有一个小窗户,单扇的木门外面除了走路踩出来的小道外杂草丛生,像极了大森林里猎人住的小木屋,但大舅再不是那个正值壮年擦拭猎枪,摆弄钢珠弹丸的英勇猎人……
此时,我只想赶快睡去,做一个清新又柔软的梦吧,在梦里那盛夏的夜除了蚊虫、虱子的叮咬纯净的别无任何烦恼,那混杂着艾草、灭虱灵以及煤油味的茅草屋依然在那里迎着困倦的我,我仍然会在姥姥那温暖的气息中安心的睡去睁开眼睛就是新一天的到来。